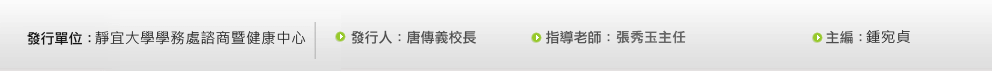我圈著身子在房間最角落,沒有開燈,大片的幽暗晦澀自四面八方墜落,跌在每塊陰影裡頭。
唯一得以倖免的是窗前一塊方形,陽光從外面傾倒而入,被切割成窗櫺的圖樣,輕巧的散佈在木質地板上,圈出幾個大小不一的形。
縮起腳趾,我向後退了些,避免那些光彈跳到身上而灼傷皮膚,趾尖緊貼著光與影交錯間最晦暗不清的那條線,只要再一點點就會越界,但也無法繼續退後。
那些目光就是如此令我恐懼。
街上一雙雙黑洞般幽暗的眸中訴說著各種不同的訕笑言語,彼此盡情交談,但我卻什麼也聽不清楚,只能被窸窸窣窣的竊語包圍,無處可逃。
每次我總急迫地尋找一片可供藏身的陰影,想把自己挪放到最不起眼的位置,但就連角落店家的遮雨棚下也太過明亮。
從那些瞳孔投射出來的是最灰暗的光、也最疼痛,我因為找不到地方躲藏,只能快步向前,感受身上傳來陣陣刺痛,彷彿再用力一些就能把心臟刺穿。
捂著胸口,我盯著自己一前一後快速交錯的鞋尖,努力把整個世界濃縮在我們之間。我是天、鞋尖是地,在這之外的所有事物都不存在。
我反覆默唸幾次,如此告訴自己,但目光從四面八方戳刺而上,痛到幾乎快讓人哭了出來。
但我記得自己並不是一個怕痛的人。
高中時在某次運動比賽中受了傷,掌心狠狠滑過粗糙的碎石子地面,擦出一圈不算淺的窟窿。
血從完好與擦傷的縫隙間緩緩流出,我爬起來盯著它看了半晌,才被滿臉驚恐的同學半拉半扯的推到保健室擦藥。
保健室的阿姨要我先沖水把傷口上的沙粒洗掉再上藥。扭開水龍頭,透明的水柱沖出,直接打在混雜著血與沙的那個小圓圈中,一陣強烈的痠痲感從皮膚深處竄出,像是許多張不知道名的小嘴一口口咬嚙,沿著我說不出正確名稱的神經往上攀爬,擴散到那些傷口以外的地方。
這種感覺就叫做「痛」,我是知道的,但也僅止於此。
有些人只要跌倒磨破膝蓋或是擦傷手臂時便會掉下眼淚,那種情緒始終令我無法理解。
為什麼會哭?
因為痛嗎?
那麼把疼痛與哭泣之間串連起來的橋樑又是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那和在閃避路上每個行人目光時的那種感覺是一模一樣的,兩者皆被強烈且巨大的無助感所包圍,疼痛不過是輔助,但也是產生這種感受的元兇。
我和那些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痛的地方會流出看得見的血、痊癒之後會留下淺到幾乎摸不出來的疤痕;然而那些視線刺向我時並不會流血,因為傷口散在一些看不見的地方,也沒有疤痕,因為不會痊癒。
陽光往西邊挪移了點,連帶著那些散落在房裡的光點也更朝我逼近,發現沒有讓我能夠再逃的地方,只好選擇側坐,讓一半的身體緊緊貼著牆面,沒有被衣料包裹的肌膚因碰觸到那無機質的冰涼而縮了縮。
靠著牆,我發現接近臉頰的牆面上有一個小洞,掉了幾片白色的油漆,裡層灰黑色的水泥裸露了出來。
伸出手,我一點一點的剝下周圍其他油漆,白色的粉塵像雪一樣緩緩地往下飄落,無聲躺在木地板上,成為大片棕色中幾個扎眼的小白點。
灰黑色的面積越來越大,粉塵越積越多,這在整個房間內顯得既突兀、又醜陋。
每棟房子剛蓋好時就算沒有傢俱,也一定會先用油漆覆蓋灰濛濛的水泥,之後可能就會視屋主喜好加上不同花色的壁紙,又或者維持原本的油漆,但每隔幾年就會重新粉刷一次避免脫落造成視覺上的不平均。
這一切都是為了遮掩。
我們習慣把自己裹上好幾層看得出來或看不出來的裝飾,儘量打扮得與每個擦肩而過的人一樣,避免在城市街道中漂浮時過於惹眼,同時也害怕自己赤裸的攤在所有人面前。
人們會選擇有各種花色的漂亮壁紙或乾淨整潔的白皙牆面,而不是光禿禿的灰黑色水泥。
而我總特別害怕被厭惡。
即使拉上一層又一層厚實裝飾的拉鍊,把自己所有灰黑色的部分好好地藏在連自己都望不著的深處,但仍害怕有哪個特別眼尖的人鑽過這些繁複的偽裝,直指那最醜惡的地方。
所以每每走在路上,我常覺得每個人都在看我。
他們都在等待時機,每雙眼都像一把及其鋒利的劍,對準我那因為時間而日漸耗損的偽裝不斷戳刺試探,若找到一點細小的破洞就狠狠刺入,把所有裝飾包裹一層層撕扯破壞,直到我也裸露出那大片的灰黑色水泥牆面。
我告訴自己要更沉默一點、與每個人都更相似一點,像吸入與吐出的空氣,儘管存在卻因過於不起眼而不被在意。
走在路上,我偶爾小心翼翼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觀察著那些壁紙的花色及漆色的白皙度,在下一次非得上街的日子裡,成為與他們相同的人,再繼續端詳整條街的花色是否有所改變,免得在不注意時變成最格格不入的存在。
牆上的洞已經被剝到與我三指併攏差不多大小,太陽沉到光照不進窗子內的地方,木地板上金黃發亮的那些點已經消失,就像走進那些密閉的廁所、自習室與房間,只有自己存在時所湧現的那份安全感。
摸上牆壁灰黑色的水泥部分,我用指尖沿著最外側的灰與最內側的白中間漫無目的地繞圈,如果某天我身上那些裝飾、那些漆了好幾層的厚厚油漆與各種不同花色的壁紙通通掉落,是否也會有人願意這樣站在旁邊,即使只有沉默也不會離去?
這個世界美麗又殘酷,我時常想站在美麗那邊,又怕真相過於殘酷以至於無法承受。因此在所有偽裝通通掉落之前,我選擇相信世界上會有個人願意站在自己旁邊。
因為世界是如此美麗。
將整隻手掌貼上水泥牆面,我還能感受得到當初跌倒擦破的是掌心上哪一塊皮膚,現在雖然幾乎已經看不出痕跡,但仍被整個身體記著。
輕輕將頭靠著牆上接近灰黑色的部分,我閉起眼,喃喃自語。
我會愛你,我說。